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意义
发布时间:2019-11-06 10:08:18作者:楞严经修行网众生依据其生存状态分为两种: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凡是有情识的,如人与动物等,都叫有情众生,没有情识的,如植物乃至宇宙山河大地,都归为无情众生。一切有情众生都在三世六道中轮回。《妙法莲华经文句》有云:“若言处处受生,故名众生者。此据业力五道流转也。”(五道指六道中的一地狱道,二饿鬼道,三畜生道,四人道,五天道。)所谓的三世六道是佛教建构的时空模式。“三世”即是指过去、现在、将来三个世界,每一住世界又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道之分,“道”的意思是往来住所。阿修罗、人、天是善道,地狱、饿鬼、畜生是恶道。佛教认为,有情众生无一例外地要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间无穷流转。同时,因为它们在三世中的“业力”的各不相同,决定了他们在每一住世界六道中的位置也不同,有情众生在不断重复经历三世的过程的同时在六道中不断轮回,所以称作三世六道轮回。所谓的“业”指的是有情众生之行为、所作、行动、作用、意志等身心活动,它能招感苦乐染净之果,即果报,并以轮回到六道中的善道或恶道的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众生在前世为人道者、现世或许上升到天道,也可能下降到地狱道,来世则有可能轮回到阿修罗道或其他众生道。至于轮回到六道的哪一道,取决于众生的“业力”。众生在过去世所作的“业”决定了它在现在世轮回中的苦乐果报,现在世的苦乐是过去世的业报.依此类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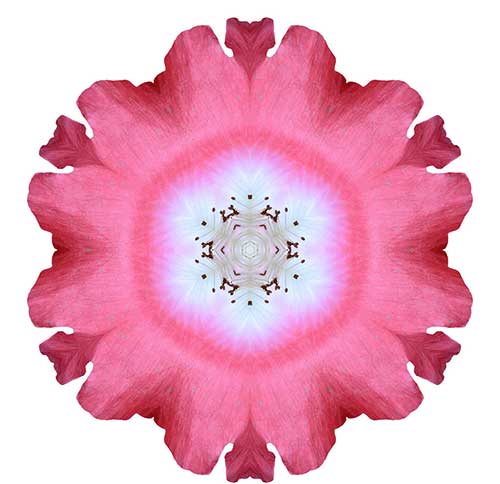
有情众生的“正报”必然同时伴随着无情众生的“依报”。有情众生依据在过去世的行为所产生的“业力”在现世获得的“果报”佛教称作“正报”。所谓“依报”是指有情众生所依据的环境。亦即生命主体赖以生存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等无情众生。佛教认为“正报”必然伴随着“依报”,任何生命体必须依存其生存环境,因此环境与生命体自身的存在是合而为一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二的,所以称之为“依正不二”。也就是说,佛教把生命体与生存环境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显然,根据佛教的缘起理论,三世间六道众生本质上是相同的,否则,畜生、阿修罗、人、天等之间就不能互换角色,所谓的今生为人,来世做牛做马的说法也就没有了依据。因此,在佛教的观念中,一切有生命的物种在本性上是相同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长阿含经》明确指出:“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
所以在《阿含经》中,佛陀自称“我今亦是人数”,意思是佛与众生本来都是平等不二的,差别只是在能否灭除烦恼;能灭除烦恼的是佛,反之,是众生。可以说,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佛教的视野更为开阔,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人类本身。佛的本生故事“王子饲虎”、“尸毗贷鸽”向信众们传达的就是“众生平等”的教义,为了拯救鸽子和老虎幼子,尸毗王割去腿上的肉,小王子舍身。或许,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这种说教有些不可思议,人的生命价值怎么能够与动物相提并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吗?然而,在佛教看来,众生平等,人与动物没有高下之分,因此,慈悲的对象不只是人类,也包括一切有情众生。在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需要受到保护的思想前提下,佛教提出慈悲为怀,善待一切生命的观念。并以此作为伦理道德的善恶标准,评判和发放众生在来世轮回果报的门票:第一善业就是不杀生.凡行善积德者上天堂,入善道;杀生则是十恶不赦的第一条,凡行恶作孽下地狱成饿鬼。《华严经》有云:“于中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总之,不杀生是佛教全部戒条的首戒。佛教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和心态去护持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一切众生,使得佛教没有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对待其他生命物种的傲慢与偏见。
一、中国佛教对“众生”内涵的发展
尽管佛教是印度的宗教,但它在传人中国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融合中逐步发展为中国的佛教。其中的佛性论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它为佛教的“众生”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即以佛性作为众生平等的理论依据,把人类对生命的关爱和平等的理念由“有情众生”进一步扩展到了“无情众生”,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点,通俗的说法就是认为不但一切有情众生,而且如草木瓦石等无情众生亦有佛性。从中国佛教的圆融观点来看,不仅人类能够成佛、有生命的众生能够成佛,而且,那些在人们眼里可以任人宰割、任意践踏的“无情众生”同样具有佛性。从逻辑的角度讲,既然佛佛平等,具有佛性的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也平等无碍。因此,在中国佛教的天台宗、三论宗以及禅宗的牛头宗那里,众生平等指的不只是印度佛教中的有情众生之间的平等,同时也包括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之间的平等。
十六国时期北凉的译经大师昙无谶翻译了《大般涅盘经》,佛经提出了“一切众生(包括一阐提)皆可成佛”的观点,认为:“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这一思想被佛教僧众们广泛接受。不过《涅盘经》中的众生指的是有情众生。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尤其是在儒家的心性理论影响下,经过魏晋南北朝有关心性与佛性的大争论之后,佛教开始形成有关佛性论的系统观点和理论,在隋唐时期就以创宗的形式宣告中国佛教的形成。其中,三论宗的吉藏、天台宗的湛然等高僧从中国佛教特有的视角——“圆融”的角度开始探讨佛性论问题——无情众生的佛性问题。禅宗的牛头宗则进一步发展出“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的观点,把佛与黄花、翠竹平等看待,使众生平等的理念更为广泛和充实。
“圆融”是中国佛学的特色和精神,所谓圆者,积周遍之义;融者,为融通、融和之义。因此,圆融从基本词义上讲,就是圆满融通,无所障碍的意思。当然,这种中国佛教的圆满融通、毫无隔历的前提是各种事物皆能保持其原有的状态和各自的独立性、完整性。也就是说圆融是干差万别事物之间的相即相入,相摄相容或者说圆满融通,毫无隔历。换言之,圆融强调的是一种对立同一关系,是一切有差别的现象、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关系。所以《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在解释“圆融”概念时说:“若就分别妄执之见言之,则万差之诸法尽事事差别,就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则事理之万法遍为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波,谓为圆融。”尽管从现象上看,世界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事物,但是它们本质上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中国佛教的这种“圆融”思想,在吉藏那里被理解为“一切诸法依正不二”。“二”即是“异”、差别、对立、矛盾。不二,亦即无差异、无矛盾。《大乘义章》解释说:“言不二者,无异之谓也,即是经中一实义也。一实之理,妙理寂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如如”是真如之意;亡于彼此即无分别之意;实义则指宇宙万物的实相。因此,一切现象的真如、实相离(不是)一切差别相,而是超越二与不二的分别,一如无二、平等无二。吉藏在这种“如如平等,亡于彼此”的基础上推论出无情众生也有佛性的观点。吉藏论证说:“以依正不二故,众生有佛性,则草木有佛性。以是义故,不但众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也。若悟诸法平等,不见依正二相故,理实无有成不成相,假言成佛。以此义故,若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得成佛。吉藏在这里明确地表明,一切众生都是处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中,离开无情众生,有情众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生命主体同生命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天台宗的“圆融”思想是通过智颤“一念三千”说体现出来的。“一念三千”是“一念心具三千世界”的略称。所谓“一念”在智颧那里指的是一念心、一心,即心的一念,是心念活动的最短时刻,用佛教的概念就是“一刹那”。那么“心”又是何物?智颇在《摩诃止观》指出“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法性也就是实相、真如。至于“三千”或“三千世界”,智额解释为: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天台宗认为,法界,如是、世间等虽有差别,有的甚至对立,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含摄的,天台宗称之为“互具”。每一界都具备(含摄)十法界,十法界构成百界。百界中每一界各有“十如是”,构成千如是。而十法界中每一法界又同时具备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这三世间,于是得出三千种世间这个数字。尽管智颤的“三千世界”看上去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是对一切万法的概括。因此,“一念三千”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探讨的是一与多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万物与心念的关系。智颤认为:“此三千在一念。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既然世界上的每一事物,本来具足大干世界的一切本性,而心即一切法,法性即佛性,那么,佛性圆融、体遍的特点便显现出来。
在智颇“一念三千”的基础上,湛然提出了“无情有性”的思想,即草木等无情众生与有情众生一样具有佛性。在他看来,既然佛性是众生的本性,也是万法的本性,那么,“言佛性者应具三身。不可独云有应身性。若具三身法身许遍何隔无情。二者从体三身相即无暂离时。既许法身遍一切处。报应未尝离于法身。况法身处二身常在。故知三身遍于诸法何独法身。法身若遍尚具三身何独法身。三约事理。从事则分情与无情。从理则无情非情别。是故情具无情亦然。”既然刹那一念具足三千世间,便是刹那一念心遍周法界,那么,佛性也具有三身,应身、法身和报身,不可能只具应身。由此,湛然的结论是:“是则一尘具足一切众生佛性。亦具十方诸佛佛性。”草木、瓦石同样不例外,与其他有情众生一样具有佛性。湛然从天台宗的圆融思想推导出无情众生有佛性的观点,把众生平等的思想贯彻到了无生命的物质世界。
禅宗的牛头宗则把老庄与魏晋玄学的“道”、“以无为本”的概念和思想引进了佛学,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道遍无情”的观点。这是湛然“无情有性”的另一个版本,当然,这个版本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众所周知,“道”是老庄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尽管包含的意思很多,但第一的要义是本体论意义的,即指宇宙万物的基始,魏晋玄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思想,试图用思辨的方法来探讨万物存在的根据。牛头禅的创始人法融在佛教“性空”的思想中添加了道家玄学的概念,提出了“虚空为道本”的命题,所谓“虚空”即是性空的别名。“道本”在法融那里也被解释为具有“离一切限量分别”的佛法之根本。他的原话是:“夫道者,若一人得之,道即不遍。若众人得之,道即有穷。若各各有之,道即有数。若总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万行虚设。”所以,方立天指出:“就此命题的思维形式来说,显然是受到了魏晋玄学‘以无为本’说的启发,就此命题的思维内容来说,也是与‘以无为本’说相呼应的,然就此命题的思维实质来说,则是般若学与道学两种不同思想的折中、调和。”
如果说,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是以心性论为出发点、从境界的视角论证“无情有情”,那么,牛头宗则是以老庄的“道”,以玄学的命题形式,把道或者佛性或者法性置于超越心物之上的宇宙本体高度。既然佛性已经成为宇宙本体,既然佛性就是“道”,那么,“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观点也就完全合乎逻辑地被推论出来。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是没有有情与无情之分的。也正是牛头宗的玄学特色——从宇宙万物的本原出发,使得佛教“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思想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对于今天的生态伦理来说,它更是提供了一种思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路和方法。
二、“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意义

事实上,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和信仰的基础,对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许这些佛教信众并没有生态伦理的意识,或许他们并不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他们严格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起居生活,在吃斋、放生和遵守不杀生戒律的过程中,赋予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人看来毫无生命迹象的植物、土地以佛性的尊重、呵护。把万物与人类相提并论,共同礼遇,甚至给予它们的敬重胜于自己的同类,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也曾经用一种敬仰或关注的目光去看待自然,把它看作具有灵魂的活的有机体。但在自然目的论观点的影响下,人们更多的时间是把人类放置在自然的中心位置。所谓的自然目的论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合目的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在动物的繁殖与生成过程中自然给予了周密的安排和照顾。而经过驯养或者野生的动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其皮毛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成“服履”,其骨角为人类的工具提供来源。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换句话说,自然界生长的植物是为了喂养动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因而,自然在人们的眼里仅仅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仓库。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和评判万物的尺度。
基督教则从宗教的角度支撑着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即把人类描绘成上帝最钟爱的生命状态,甚至把他的形象赋予了人类,并告诫人类:“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当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因此,基督教宣布说,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并赋予人类管理和控制大地的权力。所以,怀特认为西方的“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并长期“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我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因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如果说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种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观念和依靠信仰支撑的对宗教教义的解释;那么,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目标有了现实的技术保证。特别是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人们打开了崭新的视野: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物质是相同的,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于是,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观察和实验的对象。





